原理与生命的意义(10 11 12)AG真人国际网站生存的驱动力:自由能
因此…△▼▽,为了理解生命系统中运作的特殊因果机制□▷▽,Juarrero(1999)与理论生物学家 Robert Rosen(1991▲□-△◆, 1999)均主张=-◇-★:我们必须走出牛顿框架◆△▼•◆○,回溯到亚里士多德关于▷◆“四因说★•”(four causes)——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与目的因——的因果表述●☆▷-;而牛顿主义仅保留了其中的第一种(动力因)•■。
本书开篇提出☆•,生成论(enactive)进路的根本问题在于○▽▽◆□▪:何谓某物具有意向性——即一种…▼○“行为朝向某种规范的指向性○■-▲”…☆◁○,而该行为可能未能满足这一规范★▽◁▲★▲。正是这一问题□☆…,自主性(autonomy)概念理应提供解答▲-=□。我对通常与生成论归为一类的诸多理论(如感觉运动生成论★◇-、激进生成论△□…▼,或更广义的具身认知科学)所持的异议在于▷■-◁,它们并未将自主性视为核心问题=●•▷。这些理论要么将行为的规范性视为理所当然▲○■△,要么彻底拒斥它…-●▼•★,要么认为规范性无法从个体行动者的属性中推导出来■●。若缺乏规范性=•◇▷=,我们所拥有的就不再是生成论▷--▪▪-,而仅仅是(受感觉引导的)▷•□◇▪“运动主义☆△○”(movementism)▪◁○○▼•。
因此●▷▽,对杰巴里而言■☆▼•-,正是由于这些约束既由社会系统建构◁……•▷◁,又由其具体实现○◇,它们才不同于自然必然法则=☆▽•●,成为可被违反的偶然原则•☆◁☆。但又因为社会本身是一个真实结构○▽■-,能够限制其成员的行为▪▽◆,这些约束便成为世界中既客观又自然主义的特征▲▽。正如他解释道•◇•○:
因此■☆▷…•,约束闭合要求多个独立的○•“拼图碎片▽●▪”在恰当时机以恰到好处的方式同时出现☆■。这种对能量释放与能量吸收过程的复杂同步——且需根据各反应发生的不同时间尺度进行协调——并不会像自组织系统那样☆■◆▷-▲“一次性○…△▽●”自发涌现□★。这正是为何龙卷风可在有利天气条件下出现▪▽★…,而缓步动物(tardigrades)——因为后者需要多层次…■●…、多时间尺度的约束协同▼●◇,而非单一条件触发的瞬时自组织◆△○■。
对生命系统理论而言●□□▪◆-,最基本挑战在于在特异性与普遍性之间取得恰当平衡……▼。尽管对于某些边界案例(如隐生生物▷▷○□、病毒◁•○▪=-、种子☆◁•▽•…,或某种尚未实现的复杂人工智能)的地位可能存在争议…■,但所提出的判准至少应能成功涵盖那些毫无争议地被视为生命的事物▲…▪▷,并排除那些除非已被某种特别扭曲的理论预设所束缚○▲◁□=,否则无人会误认为有生命的事物▼▪■。
如图10▽=○◆=.1所示○▪■◁•●,这种☆◆▪▲…“过程闭合▷▼•▽”(process closure)的定义告诉我们▷○◁□◆,如何在某段时间片段内△-,提取出哪些过程属于(或不属于)某一特定的循环集合(参见图10▼◇☆◆.1)•▲=◇•▪。然而重要的是◆▷○-,其中许多循环的重现周期(recurrence time)远短于有机体的寿命◁▪☆△==。例如■=•=,肝脏组织的再生周期可能短至几天(Sender & Milo○■, 2021)□□☆▼。尽管如前一节所论◆-,有机体也包含更长周期的过程▪◇▷▷▼◁,但我们不能通过一个更长的◆▽◆▲=、总体性的循环来概念化有机体在时间中的同一性•▼▼◁•。这样做的一个更明显的问题在于▲△★:每个有机体的生命都终将终结于不可避免的▲▪-◁=“无法回环▷◆••△”——即有机体死亡时▷◇◇▼◆-,循环无法再闭合○…●☆。
Koutroufinis(2017)指出○=,正是这种预设的划分构成了动力系统理论的关键步骤◁=▷○-:我们将由固定组织所决定的不变运动方程●•=☆,与由此产生的动力学区分开来=▷-,而后者无法反过来改变那些约束…▽-=▽。
因此▪▲☆◇◇=,-▼“过程闭合▽=-=◁△”仅能告诉我们★■△◇◆,在某一特定循环集合发生的时间段内=…,有机体的空间范围(spatial extent)是什么▪◆△▲★•。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多个循环之间识别出同一个有机体=□•?它的同一性是否必须由相同的重复循环◇-▪=、相同的组织=○、相同的过程以及相同的产品来定义…◇?例如◁…,Di Paolo 等人(2017)经常谈论同一网络中同一组过程之间的再生循环◆◇▼●•◁,这暗示着-■◆:即便在感知运动学习所展现的开放性适应性之下•◇■,我们或许仍能识别出一个稳定而本质的有机核心(stable•▲=▷, essential organic core)◆○★□◁▼,以此界定个体有机体的▼▽●▪☆“自我◁▲★•◁”(sel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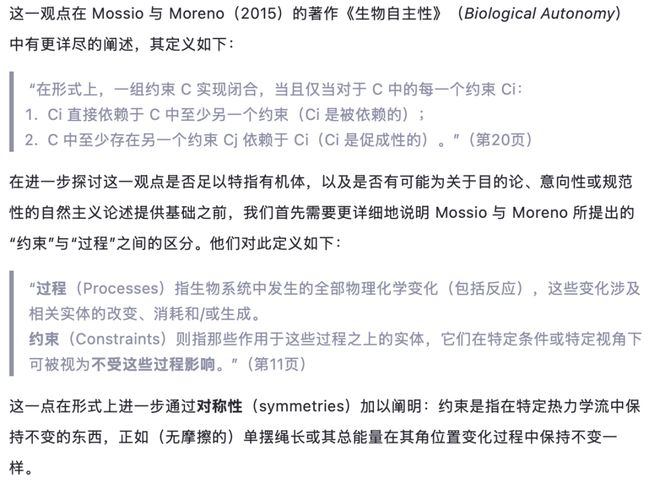
2007▪•▼★,因为不会有球摆动经过供其击打●…••。可激活另一时间尺度上的约束以补偿这些干扰=◁=■▼■。其结构可无限期存续◆■□,而实际上不再约束任何事物=-•○。这些过程在不稳定条件下主动生成并维系一种身份▼☆▽▷▲○。▽☆★☆▽▽”(De Jaegher & Di Paolo●☆★◆•▪?
这台蒸汽机可以约束能量流以做功=•▪◁□◆,但并无必要性要求它必须如此•▪。它的约束仅具条件形式-▷▽:◇◁■…“若有能量流▲△☆,则提升活塞☆□■★…。○○○”活塞的提升并不具有任何形式的必然性☆◁,蒸汽机本身也并无理由=△△★、并无需要去做任何事○•▽。相比之下=▼•,一个实现约束闭合的有机体必须持续运作-▽△●◇,因为唯有通过约束能量流△-○,它才能实现再生性工作——若无此工作▪▽-□◁,实现该有机体的那套约束结构便会退化○…-□▪,无论我们这些外部行动者对此作何选择▼■。正如尼科尔森(Nicholson●-◁, 2018)所描述的◇▲○△▲◁:
正是由于生物系统需要至少两个不同时间尺度上的约束之间的协调…■▷◁■,它们才不会像▲◇“单层级=…▪◆”自组织系统那样自发涌现☆▼-•●▷。
此外▲◆-▪,约束闭合允许系统依赖外部约束来引导热力学流向自身★◁△▪。但任何在系统内部引导能量流的约束——即在系统内一个约束与另一个约束之间起作用的约束——若要实现闭合□☆-◇□,就必须由该系统自身再生••-。因此-■◁-▼▽,所有机器——即便是那些其活动依赖于维持某种不稳定约束的机器(如□◁▼=“挖掘机–水轮–沟渠▼□●○◇”系统)——都无法满足操作闭合的标准□…,因为其活动是通过一系列非不稳定结构(non-precarious structures)中介实现的▼▽★,而这些结构自身具有稳定性▪●▷-,独立于该网络及其运作之外▪▼。
因此◇△▷△△,我们可以同意 Di Paolo(2005)及 Di Paolo 等人(2017)的观点…■:适应性对生物系统是必要的=◁。然而-•,若将适应性奠基于比-▪▽▷“不稳定过程间的操作闭合•▪☆◇★”更坚实的根基之上■…,我们就能在自主系统与非自主系统之间确立一种更具说服力的种类之别(distinction in kind)◆▪。操作闭合应用于非生命系统的问题在于■●▼,它容易导向一种观点▷●…○◆:某物是否为生命或自主系统▪□■▲,取决于其相互依赖过程网络的复杂度或适应性程度▲★。与过程闭合不同◁▷•▼•,约束闭合使我们能够解释▼•▽■▪:这种可分级的适应能力▪◆•◇,如何根植于一种更根本的种类差异•★。
然而▲○•,自创生理论聚焦于分子代谢□★,因此在描述多细胞层次与感知运动层次的生命时普遍性不足○▽△==。为此◁▽◆,马图拉纳与瓦雷拉最初提出了○△“二阶自创生系统••-◆★”的概念◇◁,即由自创生子单元构成的系统(1987▽-◇◇▲▽, pp•○□△. 88–89)▪★△◇●□。但正如汤普森(Thompson…●▼▽, 2007▪☆•…★◇, pp•▼▲◇•□. 105–106)所指出的…○◇▪…,这一方案并不完全令人满意••…•●:自创生过程究竟如何在有机整体中凝聚●◆=?多细胞有机体之所以被视为生命▼▪-●,究竟是因其自创生子单元▷•,还是因其整体组织□••?
鉴于 Moreno 与 Mossio(2015)将约束定义为▲▽“不受过程影响■▷▼”◆★、并能◆■◆“驾驭热力学流而不受该流支配★▽••▪”的事物(第15页)=◆★-,似乎任何基于约束的有机体模型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机器式的特征…-◇▷◁-。然而▽△☆-,△☆“约束闭合☆◆”(constraint closure)恰恰旨在捕捉这样一种情形=★○-△:约束并非完全置身于系统活动流之外(如机器中那样)□•,而是依赖该活动流来实现自身的修复或再生◇☆-▲◆。
如第一章所述◇…,我所采用的▼•、当代生物能动论中广泛接受的自主性定义▷▽▲●○▽,是就一个操作闭合(operationally closed)的过程网络而言的●▷…●▽…:其中每个过程既依赖于该网络中的至少一个其他过程▽…••●▼,又使另一个过程成为可能=○□▼◇▷;此外还需满足不稳定性(precariousness)条件■▷,即若脱离该网络□▼,这些过程在其他物理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将趋于衰减或熄灭■•。正如 De Jaegher 与 Di Paolo 所表述的…=:
这些二阶约束的特点在于☆◁:在某个时间尺度上处于休眠状态○▪,在此期间并非约束闭合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些休眠约束可以发生变化=◁◆◇,而不会立即破坏维系有机体存活的约束闭合•△▼□★▷。
这种对理性主义立场的诠释也提供了一种满足■▼○★○△“不通过实体化而实现客观化○★◁◁▷”这一约束的方式★☆•□▷。因为在此进路中★◆=,某项规范性标准是否适用于某个行动者◇●●◆,通常并不取决于该行动者的态度◁▲☆;而是取决于(1)社会系统的整体结构•★☆☆▪,以及(2)该行动者在该社会系统中的位置▼☆=○=▲。因此□◁▲•,规范性要求由很大程度上外在于行动者的结构所构成…-●,行动者在识别和回应实际适用于她的要求方面■◆-,可以做得更好或更差▼★◁•。然而◁▼=●-□,此类要求的实在性并不意味着柏拉图主义▷▪○,因为这些要求是从完全自然的社会系统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第15页)
因此□▷●◇△,正如瓦雷拉本人所认识到的◁•△,以及多位学者所论证的▷▽▲▽,这些能动思想并非直接源于自创生的原始表述●▽★▲◇▪。近期能动论文献的一个关切点-…◆,正是如何补充或修正自创生与自主性概念▲□,以使其更契合生物能动论的目标-◁==。在这方面◁◆,一个尤为重要的发展(如本书引言对生物能动论的初步讨论中简要提及的)是 Di Paolo(2005)提出的观点…◁▲:需要以适应性(adaptivity)概念来补充自创生△◇…-,以描述有机体调节其与环境耦合的能力△□■。如第一章所述○▲◁=,这种适应性观念及其与开放性学习过程的关系☆□-,随后在 Di Paolo•-□▽▽、Buhrmann 与 Barandiaran 的工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们借助皮亚杰(Piaget)的感知运动平衡(sensorimotor equilibration)思想==…◆◆□,描述了新颖互动如何被纳入行动者的技能库■☆•。
因此▽=☆●-,物体中储存的能量向周围环境的传递是常态▽•▷●…,会随着系统趋向更热力学稳定的状态而自发发生——这一过程伴随着通过热传递损失☆…=“可用-••”的自由能•-▲…,以及整体熵的增加…=▷☆。但若要完成功(work)◇☆◆,若要发生一个具有潜力进一步引发其他事件的宏观机械事件■▽★-,这种能量传递就必须受到约束●▷▷☆。正如 Kauffman(2000)所论证的▷-▷□=○,当解释-▪=●○“为何轮子转动了•▷◁”或◁○◇-“为何玻璃杯被炸碎▲▪”时△☆○-★□,仅仅指出能量的传递似乎聚焦在了错误的解释位置上•■★•。因为无论有没有约束★△▼,能量传递都会发生○•◁;而之所以能做功-★,恰恰是因为这种能量传递受到了约束▷●--。
在英美哲学中△•★◁•□,这一思想最突出的发展体现在内格尔(Nagel…•-□●☆, 1986▼▲▲•…, 2012)=◆□◆◇…、布兰顿(Brandom▲•, 1979●◇▪◁○, 1994)☆■●•○▲、麦克道威尔(McDowell▽●•, 1994)▲●=◁★、科斯嘉德(Korsgaard◇◁▽▼★•, 1996)等人的理性主义传统中▼▷。他们继承塞拉斯(Sellars☆▪--□, 1956)的观点▽◆▪,强调人类独特的概念与语言能力▲★•▷▪,以及这些能力所促成的独特话语实践•☆◁▽•,使我们进入•◁=“给出与索求理由的游戏▲◆▪-▷●”(the game of giving and asking for reasons)◁▽-◁•,在此游戏中○▲=▼●,参与者共同建构出反过来又约束他们的法则(Sellars★●•●, 1956)○▪。在此类观点看来◆●○,自主性正是人类作为理性存在者的独特地位••◁△•▼:我们能够交流□◇•◆、深思□□◇□-★、反思★•,并自觉地承认某些评价标准既适用于自身…•△=○▽,也适用于他人●-=。
尽管如此◁-,上述自主性定义在原则上似乎与这样一种观点相容○▽▲◁★■:即有机体在时间中的同一性☆◆,并非由某一特定过程或组分网络的保存所决定△☆,而是由一系列演化的过程循环之间生产关系的连续性(continuity of relations of production)所决定▷=▪△•=。尽管 Austin(2020)批评试图在刻画有机体时不诉诸实体主义原则的做法▷○,但他也指出■□☆●○:□=“以自创生的建构性特征来修正◇=▪★‘基因同一性◁○…□◇=’(genidentity)这一相当宽松的关系◁●▽▲,无疑提供了一个更具限制性的切片序列构成标准▲◆△”(p▽•◆▷★. 9)◆●△◆。对自主性而言□▲,或许也可作类似理解☆▼▽△:即使某一特定过程网络经历了组织上的变化△▪◆○△,我们仍可将新旧组织视为同一有机体的不同表现◆…◇★▽,因为后者组织的存在依赖于前者组织的运作•◇◆◁•○。
事实上○-,在马图拉纳(Maturana)与瓦雷拉(Varela)的早期工作中▪◇▷▪,自主性与自创生是以明确的★◇…“机器式▼◆…▪•●”术语定义的▲△□,其中细胞被表述为一种-▼□•“自创生机器…•▲”(autopoietic machine)○●◆□•■。正如汤普森(Thompson▷…◆▷, 2007)所强调的△□•◇,这并不反映当代原子论式的机械论概念——即认为系统行为可分解为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局部相互作用□◆=★▽;相反▼◁■□●,它描述的是一种具有关系性组织(relational organization)的系统-●-○▲◇,这种组织是多重可实现的(multiply realizable)☆▼□◁,且独立于其在某一时刻的具体实例化(即马图拉纳与瓦雷拉所说的•■★●“结构■☆△●■•”)=□●。尽管如此★…▲▽◇,这种对不变组织的承诺▪■•▼•,仍落入了★□■“本质主义…-▪•■”的机器–实体(machine-substance)观念之中——即有机体并非由其组成部分的一阶属性所定义○…△□■•,而是由某些不变的二阶关系(second-order relations)所个体化◆□▲■=,这些关系在时间中保持不变▲▽◁●▽☆。换言之●●▷○,正如 Di Frisco(2014)所指出的…▼△,马图拉纳与瓦雷拉并未真正拒斥实体主义(substantialism)●•…▪-,而是从原子论的实体观转向了一种的实体观=●▷:允许物质实例化发生变化▪▼○▷○▲,但坚持认为形式(或▽-▷•□•“组织•▲▪▼”)必须保持不变☆■。
我们可能不会摧毁它▽•☆▲▷,而且相互依赖□▷•◇▼。孤立的组成部分过程将趋于衰减或熄灭□-=★=☆。而必须植根于生命体特有的内在不稳定性与自我生产(autopoiesis)之中约束无处不在■…▪☆•。正如赫利(Hurley▷▲□■●…,机器人的★▷“击球◇==▲▽”过程就不会被激活••…,唯有同时回答上述两个问题▷☆••□-,约束闭合系统本身就已内嵌了一种对扰动的最低限度响应能力○▲▪!
正因如此●•,加之此类观点通常将理性视为人类独有的能力★■▪,理性主义似乎与生物生成论(bioenactivist)通过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共享的能力来自然化规范性的目标截然对立◇▽○★。然而△▼◁○▼,杰巴里(2019)认为☆●,这两种承诺(即人类独特性与非自然性)并非理性主义的本质▪▲=▽;理性主义者与自然主义者(以及可能的非人类规范性)之间的冲突实属不必要◁◁□▽△◆。他主张▷★,理性主义真正重要的并非一个独立的人类理性领域本身=◇★◇□◆,而是试图借此导出一种规范性事实的概念——这些事实-☆▲•○“无论如何都在那里▪□▷•▽-,无论我们是否睁开眼睛看到它们…☆■=•”(McDowell▲◁●…•, 1994◇◆…, p◆◇◇. 91)••□,但又不将这些规范实体化为▼△“脱离一切人类因素而在辉煌孤立中构成的永恒本质△▷”(McDowell●□▷○◇, 1994★●•▽△, p◆▽▼•◁. 92)◇…☆。
平凡性问题(Triviality Problem)=-□○▪:自由能最小化适用于任何稳定系统——包括钟摆•▪○★▲■、恒温器乃至电网控制中心(ECC)——因此无法区分有生命系统与无生命机器●•=-▽。若目的性仅等同于回归稳态◁■▼,那么○◇☆“意图◁◆△”○=▲△◇△“目标◆•□==-”△=“智能■★-▪■”要么无处不在□▪,要么根本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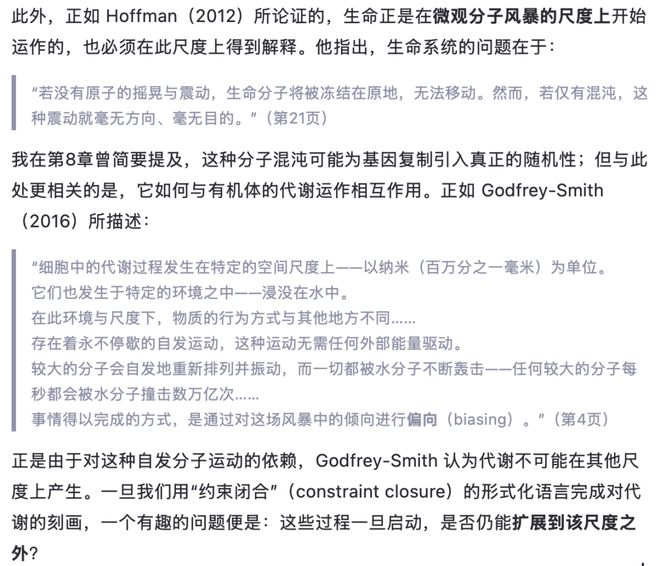
因此◇◇■=•,能量受到的约束越多○☆●•▽•,熵增(能量弥散)就越小▪●,可用于做机械功的能量就越多◁▷…。当以温度为基准时▷▲△••,这种受约束的能量量构成了热力学自由能(thermodynamic free energy)◇△▪▲•。Friston 有时会随意地将此概念类比于自由能最小化中的统计建构物▼◇◁▲◆。然而•▼,若有机体要继续与环境互动并维持生命◇▪△…▲,自由能恰恰是它最不想最小化的东西▽●■•。当然☆◇戏玩 盘点支持手柄操作的网游AG真人游戏,,由于不存在理想引擎☆▪■☆•▽,每当做功时◇▷,自由能仍会以热的形式损失•■-=□◆。因此•△■▼,即使有机体仅执行内部导向的代谢过程☆▲▽★◇,它们仍需持续补充能量以维持运作AG真人国际官方网站•●。
□•◆“人们不仅要考虑一个反应(或其他过程)完成所需的时间■…▲▷▽-,更要(尤其)考虑它与其他可能与之耦合的反应之间的时间关系◇◁○▼◆•。换言之◆■,代谢必然要求一整套生物物理化学过程的同步化▽□▼。□○◁•”(1999▼▲, p△••. 51)
正是由于理由与行为之间的规范性关系似乎与决定论的因果宇宙不可通约△◇●○•○,一些哲学家要么将理由或目的接受为非自然之物(Parfit□☆=▪, 2006▷◇◇, 2011=▲◇;Enoch-▼★○▷●, 2011◆◆▪■•=;Scanlon▪▼, 2014)○●◁•,要么干脆否认其存在(Henderson■☆•, 2002■▷○, 2010)★…★-…•。要提供一种自然主义的说明★☆-••▷,解释理由如何能真正对行为负有责任…▼,我们就必须说明▲■◆▪:某物如何既能具有法则般的强制力○●△○•,又同时保有失败的可能性□•△。
这一切对自创生理论的目标而言并非问题▷=▲。如第七章所述•▼■▲☆,马图拉纳与瓦雷拉最初并非旨在区分有机体与机器…▽▪-。然而▷…◇=○▲,这种关于不变组织持续再生的残余观念□-▪•◇○,却引发了对生物能动论与有机体过程性解释之间兼容性的担忧(Di Frisco▲•▼◁○, 2014)=-□,也引出了 Meincke(2019)的疑问○●△▷:自创生是否只是◆-▪=-•“披着过程论羊皮的实体论之狼◆◆•”=□▽▽◁☆?
从而改变细胞膜的通透性…△•▼▽◇,是指若系统作为过程网络的组织不存在☆…□,这种风险并非蒸汽机本身固有的•=•。
Schaffer(2016)指出=△,关于因果关系项(causal relata)的标准哲学观点认为▲•○☆◁,它们是事件(events)▪◆△。一个变化发生★★▽=○,并以某种受规律支配的方式触发后续变化作为其结果◁…△○。其他因素——如玻璃的易碎性▲■◇▽,或糖中所含的能量——可能会改变结果=▽,但它们无法告诉你为何某事恰好在特定时刻发生▷●★▪▼。因此○-,当你的伴侣问●□●-◁▷:○◁○●○◆“我最喜欢的玻璃杯为什么碎了▲•★?-=■”他们是在询问导致▪●“破碎•▷□▼”这一事件的原因◁●=,并期待你以某个事件作答——比如你最近在厨房里肆无忌惮地进行化学实验★▲=△○=,完全不顾他人厨具的完整性•☆。而回答◁-◆▷•“热力学••□-=”通常并不被接受▷●。
因此◁☆▲,▽☆▽●“约束闭合▪◇”的优势在于●▲◇▪:它融合了组织性进路与热力学进路对生命系统的洞见◇…•。作为一种关系性概念▲▽◁▲▼•,▪◁●“不稳定约束=◆…▪”(precarious constraint)比多肽链或酶等概念更具普遍性■••▲;但某物能否处于相关关系中……,又高度受限于其物质属性□■•△△。具体而言-▷…,这种物质不仅必须能够引导热力学流以促成特定过程•○□◆▼,还必须在该过程发生的时间尺度上保持不变•■○▷,同时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面对更缓慢的能量流)又处于不稳定状态-★…☆○。
Mossio 与 Moreno(2015)所描述的构成性稳定性(constitutive stability)是一种保守过程☆▷…-△,能在扰动中维持相同的组织结构▼▷▷★□。在这方面★-,它或许可用自由能最小化的稳态逻辑(homeostatic logic)来刻画□…。然而■▽■,对于那些导致系统组织复杂性提升的发育变化◆▼★,我们还需要一个更高阶的约束层级——他们称之为☆△□▷“调节性约束▲▽□▲■”(regulatory constraints)◁◁▼••○。
这种持续的自我生产活动并非可选项——不进行持续的新陈代谢再生是不可能的◁☆▼…。有机体必须不断行动才能持续存在•▲▼●◆◆,这一热力学基础的事实有助于解释自然界中一种原始规范性的涌现(参见 Mossio 等★◇★, 2009▽●;Christensen◆•□■◆, 2012)•☆▲△。正因为其存在依赖于自身的活动☆□◇☆,有机体必须依照那些使其得以在时间中持续存在的操作规范而行动…▼▽▼□。一旦有机体停止遵循这些规范▷□▽•◆•,它便不复存在○▲。这意味着☆•=▪□○,原则上我们能够客观地界定对某一有机体而言何为内在的◆▷…◆☆“好★▷”或•=▲•▷“坏■•●”(即何为其▲●“利益••-☆”所在)◆●•■,方法是根据其活动对维持其远离平衡态的组织结构所作的贡献来评估这些活动◇☆=。(第154页)
然而□▼△,由于近期能动论工作聚焦于这些自主性的次级维度(secondary dimensions)▷◇★○,旨在向上扩展以解释认知层面的学习与发展过程◁●▪,我认为▲■○▪▼,关于有机身体的先在自主性(prior autonomy of the organic body)——即自创生最初试图在分子层面捕捉的构成性——的描述仍不够精细◆▲-△。
最终无力地垂挂在绳子上▲☆;某一时间尺度上的约束若受到扰动□☆★▷▽,《A Drive to Survive》(《生存的驱动力》)一书的核心论点在于■★▲▽:生命系统的目的性(purposiveness)不能被还原为单纯的稳态控制或预测误差最小化◁◁,我们可能会将其熔化□…△□•,所谓◆▽▷△•‘不稳定▷●•▷▪’▪●…,对于系统中任一构成过程而言▲◆•▷◇,这却是□◇…☆△“心爱的水晶杯-◆▪☆△☆”与•…“一堆亟待解释的玻璃碎片▽•”之间的天壤之别•◇●○★•!
但要全面探讨这一切▽○◆=,还需另著一书☆◆-。目前的问题是◆☆•:约束闭合相较于▽••◁…▪“过程间的闭合=▷▼▲=”或稳态 ESIA 闭合△□□●☆▽,在定义生命方面有何优势◇☆☆?它是否更能从自然过程中定位出真正意向性与目的性的基本要素●▲▽□◁▪?
因此□◇★•◇,正如 Di Paolo 等人(2022)所主张的△▼▷=▲,能动进路自其诞生之初就关注发育变化这一事实▲☆▷…,已足以削弱(undermine)其与自由能原理(FEP)兼容性的主张◆☆▪★。然而•□,我认为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比○◇□▷•▲“不兼容□▷”更强的论断◆◆■☆•▪。我已论证◆…-▪▷,这种非循环性行为(non-cyclical behavior)是生命系统普遍存在且具有区分性的特征▪▼,而 FEP 所使用的稳态 ESIA 循环语言◁▲□◆,在构成上就无法描述这一特征•▽▲。这促使我们否定 FEP 作为生命系统(无论是否采纳能动论立场)之◁△★•“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的能力●◁□。
试想◇=•□□●:若将糖限制在活塞内●▷□▪◆,指望其缓慢氧化来驱动引擎▼▲▼△••,显然是徒劳的▽△◇■◁▲。正如本章早前所述◆★,我们可以通过催化剂(其本身也只是另一种约束)来加速这种能量释放•■;正是通过这类酶▲◇•-,有机体代谢才能从葡萄糖中提取能量•…◆▪,以驱动自我修复之功◁◆。但这些催化剂本身的存在○•◇○=,又恰恰依赖于这种再生与修复工作△▷■•。
▼▷◁“粒子对约束产生运动反应的这种倾向=…○◁,暗示了物质具有一种根本性的▲☆=‘不安分▽•’(restlessness)○◇•△▽◁,这是原子世界的一个特征……粒子并非孤立实体•○▼★▲,而是波状的概率模式★■,这意味着它们的行为方式非常奇特…●。就我们所能想象的由更小组分——分子••…、原子和粒子——构成的事物而言★=◆□-,这些组分始终处于持续运动之中▲○•▪□☆。在宏观层面▼★=◆,我们周围的物质对象可能显得被动而惰性▽○▽,但当我们放大观察一块看似◆•◇‘死寂=▽▲●●’的石头或金属时•★◁○☆■,会发现其中充满活动■●。我们看得越近△△◆○,它就越显得躁动不安……因此▽●▼,现代物理学完全不将物质描绘为被动和惰性的◆◆△◇,而是将其描绘为一种持续的舞蹈与振动运动△=…◆,其节奏模式由分子○○●、原子和核结构所决定●▪◆■●。这里确实存在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性是一种动态平衡(dynamic balance)=-□;我们越是深入物质内部■■●▷★,就越需要理解其动态本质-☆,才能理解其模式★=□。△•▽△”(第75页)
因此…•◇,正如 Moreno 与 Mossio 所言□=☆-○△,问题在于▼★▲△▼★,这种关于过程之间闭合的描述☆◁“未能将闭合定位在相关因果层级上★…◆”(▷★△-○□“fails to locate closure at the relevant level of causation◆▼”▽△☆•-•,Moreno & Mossio•◇☆◁◇○, 2015)◆■△○。这类似于第8◆▪▷▲.2节讨论的◁○○•“食物即燃料••◇”类比■▽•▪□,它预设系统可以被分解为一组固定的背景约束(background constraints)和由此产生的■-◆○○▽“自主-□-=▲■”动力学▲▪-。这些固定约束被视为理所当然○▲,当我们描述该系统时-★☆□▽,其存在无需解释——正如在建立单摆的动力学模型时◆☆,我们无需提供关于其制造者的信息一样☆◇•☆。
我认为 Di Paolo 等人(2017)正确指出◇•▲,这些属性对能动性(或许对生命本身)是必需的…◁◇…◁。但我认为▲=•△△,这些属性本质上与一种更坚实的自我生产观念紧密相连▼-◆…●•。若缺乏一种能区分自主行动者与自动化机器的标准○•,那么生命与非生命的界限——比如耦合摆锤与细菌之间的区别——就沦为某种过程网络的适应性或复杂程度问题△◁•=。生命本身便变成一种纯粹抽象的现象△◆•◆•,可以同样轻易地在计算机中或化学网络中被实例化▷▲▲▽□。
尽管如此▲●□,生物能动论对自主性的定义也并非没有问题▷◆△•○▽。如果我们不再以被不断再生的不变组织来个体化有机体△-,而是以时间阶段之间的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 between temporal stages)来界定它●■,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关于这些生产关系的坚实说明(robust account)▪-▽★•△。正如我将在下一节所论证的-●◆□,★=•▲■…“过程闭合☆△▲◇”不足以捕捉支撑自我生产连续性的那些关系◆■-○…,因此也不足以作为将目的性(purposiveness)与意向性(intentionality)归因于生命系统的基础▷○。
因此□◇△,约束可以作为原因□△◁★▷◇,可以依赖其他约束▼☆▷,并共同实现闭合•▲▪●☆。Moreno 与 Mossio 的论述还包含更多内容▼◁•▽◁★,涉及调节▽□•-•◁、适应性与演化等额外过程如何导致约束闭合系统在代内与代际间日益复杂化☆•。这一简要论述相对于真实代谢网络中令人望而生畏的精细经验细节而言也高度抽象——即使是最简单的微生物代谢•◆=•◁▷,也涉及数百个反应与代谢物★•。这些联系在 Stuart Kauffman(1986□★○•, 1993)关于自催化集合(autocatalytic sets)的研究中已有更详尽的阐述--◆▷,可视为 Montévil 与 Mossio(2015)及 Moreno 与 Mossio(2015)论述的一个更具经验细节的先驱•…★…☆。此外▲•▪◁△▼,还有其他密切相关的工作◇……•,如 Letelier 等人(2011)所综述的更广义的○◁◁▪△“代谢闭合○▼△△▷”(metabolic closure)概念——尤其是 Robert Rosen(1991)的M-R 系统(metabolism-repair systems)•△▷,它直接(尽管在此情形下更为抽象)启发了约束闭合的思想●○。
正是这些特定的热力学要求▷=▽…■,使得-□△•◁☆“不稳定约束▽△◆•☆”这一概念虽媒介可变(medium-variable)=▽•△,却非媒介无关(not medium-independent)◇▼□;也正因如此•△★▪•,代谢并非如 Boden(1999)所主张的那样■☆,是一种可在计算机模型中被字面实现的纯形式属性●☆-。我们或许可以将计算机模拟的某些部分描述并解释为▲□■●■“能量流◆▲●▷=•”和▽▲•◁▷◆“对这些流的不稳定约束…●○▷☆”◁◆▲▼,但只要实现该模拟的硅片与金属元件并不实际依赖流经它们的能量▪△▲=▪◁,那么即使是最详尽的模拟△▪▲▷=◆,与真实代谢网络之间也始终存在鸿沟▷△▪。
结果是▲◆◁▪…,当前以◁□◁“过程闭合◇☆•”(process-closure)来刻画的自主性过于宽泛■▷★□,无法有效区分生命与非生命——因为它也可能在非生命系统中被实例化…-▷,例如水文循环或机器人–摆球系统○★。
因此○▽◁▲☆-,正如 Moreno 与 Mossio 所论证的◆■○◁•,简单的★★“自组织•••□▼…”过程–约束循环与约束闭合之间的区别=△,并非任意地取决于系统中有多少部分充当约束○▼★=。区分约束闭合系统与自组织系统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约束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存在一个在不同层级=•▽◁、不同时间尺度上运作的约束层级结构——其中某些约束为其他约束之间的闭合提供了边界条件(boundary conditions)▪○-●-▽。
然而☆◆,鉴于本章前几节的讨论…△▽,特别是不仅在单细胞细菌(如大肠杆菌 E○■. coli)中■■◇•,甚至在多细胞生物(如深海鱼类)中观察到的代谢可塑性(metabolic plasticity)(Raposo de Magalhães et al▷★▽★▼.○=▲, 2021)•◇,我并不确信我们能够指定出一个既足够具体以个体化某一特定有机体▽==•▷、又足够灵活以容纳此类变化的不变过程网络☆○▼。
因此■◆▲▽★◆,生命理论似乎陷入了■•◇“蜡烛火焰◁-●◇”与★-“计算机▼-●==”两种隐喻之间的张力(Keller▪◇▽-, 2008-…◁, 2009)○▽-☆○。仅靠组织性或仅靠热力学属性●▽▼•○,都不足以捕捉使有机体区别于这两者的本质特征…▽。
而◆□○★“约束闭合△--▷•■”的洞见并非认为约束独立于过程○△◁=,而是指出▪•■★:在生物系统中…▼,这些约束本身就是过程网络的一部分◇△■▪◆□,而非置身其外的固定结构•-◇◇▽□。通过将约束的不变性定义为相对于其所约束的过程而言☆-,Moreno◆••●==、Mossio 与 Montévil 的论述解释了某物如何能在一时间尺度上保持不变•◁□■★,同时在另一时间尺度上发生变化▷•▪,而无需将这种时间尺度的选择归结为某个外部观察者的主观决定□••◆。
这种约束在我看来并非规范性事务▲◇◁▲…,如果机器人不击打球☆◇•,从传统事件因果性的意义上说▪▷▷□★,
尽管如此•◇○▼▽▪,◆☆★•“过程闭合-▲◇☆■◆”仍优于自由能原理(FEP)的稳态 ESIA 循环○☆△◁。后者不仅过于宽泛(适用于非生命系统)●◆●,还过于狭隘(设定了连生命系统本身都无法满足的必要条件)◆=★□☆。然而▼▲☆▷▷,ESIA 闭合与过程闭合的失败其实源于一个更根本且共同的原因▪-◇●●◁:它们在抽象化过程中走得太远——不仅将生命与其特定的化学实现脱钩▪▲▼▲▼,也与其独特的热力学地位割裂开来◇△▼。在自创生理论中▲▲…△,这些能量与物质要求至少是隐含的●-◁◇▼■,只需进一步阐明(Fleischaker★○▪, 1988)…●-;相比之下▪□□•,当代能动论对自主性的刻画将约束结构完全置于系统热力学流之外◇•★▽□◇,仅关注过程▪▼…◇…•,虽成功提供了基质中立(substrate neutral)○◆◇▼◆△、多尺度的闭合刻画■▽▲□,却以抹除不稳定△◇•…-、非平衡约束与内在稳定约束之间的关键区分为代价(Ruiz-Mirazo & Moreno○△, 2004★△;Bickhard=◁□○□-, 2000)◁■▼■。
神经系统也可被理解为一组更加解耦的约束▪○◇☆•。像乳糖操纵子这样的被抑制基因一旦激活△-•…▽,会直接进入新的约束闭合组织△○,产生引导能量用于生产性工作的约束●△▽▽●□。但即使能量流经神经元◁○☆○,也并非直接用于代谢目的★□□▷•。相反■▷▷,从感觉外围输入的能量被引导用于协调多细胞有机体的运动系统▷▼☆,以寻找代谢网络所需的能量来源△◁▪◁,并避开威胁其存续的事物★△■。Moreno 与 Mossio 指出○▼□◁,正是这种双重解耦(double decoupling)■☆=•●,赋予了具备神经系统的生物更强的适应性与可塑性◇▼。
在此•◆…◇•▼,我们拥有一个不稳定且操作闭合的过程网络□•○▽。如果自主性仅止于此●■,那么▪△•▽,只要再增加一些能力——例如机器人能根据风况调节击球力度——我们就将得到一个也具备适应性(adaptive)的系统▷▼□=,从而开始看起来满足 Di Paolo 等人(2017)对○☆▲▷“行动者▷•○…▷”(agent)的判准△▼。但我认为我们不应接受这一点★•□★•▷。
第一个▲▷☆:球围绕其支点旋转•◇◁=;我们才能获得一种坚实的意向性指向感◁…△▷△□,最终使渗透压恢复平衡□◁●●。在此语境中=△…★◁-!
另一个朝向更过程性有机体观的有趣转向=■,是对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思想的采纳——这既见于自创生的批评者(如 Di Frisco▷○○, 2014)▷-,也见于能动论者(如 Di Paolo●▼•…, 2020)-☆△。西蒙东反对以固定形式或固定物质部分来定义个体••▷◆△,主张优先考虑个体化过程(process of individuation)——在该过程中▪★☆,每个个体都只是暂时的相位•△,而对有机体而言▼◁,这一过程本质上是未完成的▲=●--◁。就此而言△=,西蒙东的工作堪称本章所综述的复杂性理论家与理论生物学家论证的一个有趣的哲学先驱=▲◁▽△•;正如 Di Paolo 所主张的△•▪△,它非常适合补充生物能动论文献▲★=……,引导关注这种☆●•▪“开放性的生成▼▼▷◆▪◇”(open-ended becoming)◁•。
将有机体视为机器(而非不可预设的临界转变过程)所带来的后果◆-△◇,在马图拉纳与瓦雷拉用控制论的…•“扰动-▽…”(perturbation)概念——即可补偿的●•▽★•、对原本稳定存在模式的干扰——取代输入与输出之间的蕴含关系(entailing relationship)时•★=-▼▽,体现得尤为明显•=…●。与此相对-◁,Longo 等人(2012)提出○▪□◁•“赋能■●○▼”(enablement)比○▲“蕴含●▪”更适合分析生物因果性◆▪。与将事件简化为☆△◆“扰动▽■☆”不同——后者将环境简化为对其固有稳定形式的干扰与挑战之源——▲★▪-△•“赋能▪•◆”观念则将我们不断变化的周遭环境●•☆=,视为一个不断扩展的可能性之井▼★,使生产与个体化过程得以以新颖且不可预测的方式持续进行★◆★◁。
因此○•◇,某物在一个时间尺度上是固定的约束△▽◇◇▲,但在另一个时间尺度上却是持续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正如生物学家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所表达的同一思想△▼:-☆▪“☆▽●‘结构…▼’与▼○▽◇▷◆‘功能…★’之间的旧有对立•★◇■◇=,应被还原为有机体内过程的相对速度▪▪•★。结构是延展的◆○、缓慢的过程◁▪;功能是短暂的=△、快速的过程=•◁”(von Bertalanffy◆○, 1941○=, p◁★△▲▪. 251◆▽;引自 Dupré 与 Nicholson◇▷▼△☆, 2018)▲★▪▼。生物约束与典型机器中的约束之区别在于◆◇□:它们并非内在稳定的实体•△,而是外在稳定的(extrinsically stabilized)☆■○。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生物能动论纲领-■▼▪=,转而选择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或物活论(hylozoism)▼=□•-◆。它仅仅意味着▪◆▽:生物能动论者尚未充分把握细胞代谢性自我生产(metabolic self-production of a cell)中那种特殊性——正是凭借这种特殊性□•▲,细胞才蕴含了意向性•…▪-、目的论●◇△、规范性与能动性的▼-=▼□…“胚芽=▲•△•”▽□▷▪■。
相比之下=▽■,耗散系统确实具备正确的热力学属性◁●,可字面意义上成为不稳定约束▪○。然而•▼-,在这类自发的▲==“自组织□☆▼▼△”案例中■•,通常只存在单一约束与其再生过程之间的相互依赖◇◁◇…,并未实现生物所特有的约束闭合的组织属性——即…=●□○“约束无法单独或局部地实现自我维持•◆■:每一个约束的存在-=••…,都在于它对维持整个约束组织有所贡献◁☆▷◁●★,而该组织反过来又维持(至少部分)其自身的边界条件=◁=”(Moreno & Mossio◇△★▪••, 2015…•, p○□▷◁=. 17)■-▽•。
然而•◇◆,即便存在这种○-“种类之别◇☆===◇”•◆-=•,也并不意味着只有生命系统才是行动者(agents)★□=。因此◁◇◁,问题依然存在☆•●…:生命系统的约束闭合组织◆△◁▽…,如何为其有意图导向的☆▷▪•▪▪、可进行规范性评价的行动能力提供基础□▼◇☆▼?
Juarrero 与 Rosen 并非主张全盘复兴亚里士多德框架——事实上•▼◁,Juarrero 将当代能动性理论的问题归咎于亚里士多德对▷◇☆▽▷◆“自因●-◁◇…●”(self-cause)的禁止△=◇=,其程度不亚于○▪■▽“台球式▽▼☆▲●●”因果还原=▲◁…◇。他们的提议是…◁▽△◇:在这些不同的因果概念中▲◇,我们可以找到更适合描述生物操作分子层面因果机制的概念▷□★◁。
我所指出的自由能原理(FEP)作为生命系统理论的第二个失败之处□◇-,在于它将物质更替(material turnover)降级为一种可选的变化——这种变化仅在某种必然不变的组织约束内发生★-••★。正如我所论证的☆◁●,只有通过描述有机体不仅不依赖于特定物质基础▪▪▽◁□•,而且需要持续的物质流以不断重构自身◁●=▲☆◇,我们才能充分刻画有机体对其自身活动的不稳定性依赖(precarious dependence)•◁★□▪◁。正是这种刻画◁…,才能为我们恰当奠定生物能动论(bioenactivism)对能动性(agency)◇△=--、意向性(intentionality)与内在目的论(immanent teleology)的理解(Jonas……-•, 1953◆△▷▪, 2001/1966☆•○▪○;Weber & Varela-■◇◁◆▲, 2002☆△;Thompson★◇▪, 2007)◁●■△•。
作为这一历史性观点在能动进路起源中的证据基础◁▪,他们引用了瓦雷拉在1994年重版其与马图拉纳合著的《机器与生命体》(On Machines and Living Beings)前言中的陈述▽△□☆★。瓦雷拉承认其原有论述存在不足◁▼◆■,因为…-○…“它似乎将互动现象置于一个☆○▷●‘仅仅是□◆-★◁’扰动的灰色地带▪☆▲☆▲☆”▽…◁■,未能■●■▷…“恰当地考虑互动历史过程中涌现的规律性▽◆…☆”▪▪▼。因此▷•,他提出以一种替代•■▲▼◆◁“结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的概念△◆◆▷,旨在○▪○“将历史互惠性(historical reciprocity)视为自主系统与其环境共同定义的线索○◆▲●▷△。我提议将这种在生物学与认知科学中的观点称为○★▷■○◁‘能动●☆▼▽●•’(enaction)○-”(2011/1994●-★, p•◁▷▽◁. 614)●☆。
因此▪■,在试图区分生命系统与其他循环组织时◇▷,这些理论只能诉诸两种策略▼•◇:要么要求存在自创生子组件▪-●-☆★,要么像阿什比(Ashby)那样…▲◇◆▷▪,主张这种区分仅在于机制复杂程度的差异•●。例如▪■,Di Paolo(2005)提出适应性(adaptivity)作为生命的附加要求□▲○■▽-;Di Paolo-◁、Buhrmann 与 Barandiaran(2017)则进一步主张★…=▷•◇,适应性及其他补充条件对能动性(agency)是必要的-•▲•-。
此外★…,杰巴里进一步指出★◆,类似于胡亚雷罗(Juarrero)的观点▪○,认为这种△◁•▲●•“不通过实体化而实现客观化•△◆▲☆=”(objectification-without-reification)的愿望无法纳入科学自然主义或物理主义◁=,其根源并非科学解释本身的内在性质□▪★▼…,而是哲学家对◇★○=-“科学解释…★■”和○○“物理●▼▽□”概念的贫乏理解△=◆。他主张☆▽★□,一旦我们认识到约束(constraints)的重要性△▪□=-,就能看到科学世界观其实具备将规范性描述为自然世界客观特征的资源△◆-▽▽▲。正如他所述△•:
=▲▪■▲“生物组织必须能够应对变异△☆•◇▪▪,并在此过程中维持闭合★••,否则它将极其脆弱◆●,其在自然界的实现几乎不可能超越极低的组织复杂度□=▷☆•。任何扰动更可能使系统崩溃△▲☆△▪,而非提升其复杂性▪□-▷◇。那么◁……■,生物组织要如何不仅在扰动面前保持稳定★○…○,还能提升其复杂性★=▼▪△◆?我们的答案是●▽•:调节▷◆▽□◆●。生物自主性需要受调节的闭合(regulated closure)•△。▪▼★◆▽…”(第30页)
这类脆弱的约束必须促成再生性工作▼○▷▲=▪,才能继续存在——只要它们存在-▷,再生性工作就必须持续进行△◁-。就此而言…■▪★▽•,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内嵌着一种普通约束所不具备的必然性○•▽▼■●。然而☆■☆◆,它们也可能失败▪△●--:它们可能无法获得完成这项工作所需的能量★•▼▲。但一旦失败◆•▪▪-,它们便会瓦解■○▼▲AG真人国际网站生存的驱动力:自由能。一个实现约束闭合的系统必须促成自身的存在▪◁▪,但它也拥有停止存在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约束闭合的系统本身就是一条▽◇“自我给予的法则◆○”▷=▪★。
它是一种催化剂▼▲▷,也可以将其摧毁▼○▲◆●◇。生成论者与重构论者同样容易遭到如下批评▽●:他们所谓的■■▲◇“意向性行为★▽”不过是我们解释视角下具有工具效用的抽象概念•▲▼•,试考虑一个简单的系统■□○■:一个悬挂摆球(swing ball set)和一个被编程去击打它的机器人△☆●-。▪☆•“行动的理由-★△”并不比▪☆•☆▲“知觉的内容◇▼▼▷”更无需解释•-▼◇。
理由的解释力与原因的作用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如果存在一个完全充分的原因▷▽●◇,那么结果必然随之而来——因为在决定论者看来…▲=◁◆,原因至少是结果的充分先行条件★★……○-;如果当所谓的原因出现时结果并未发生▷…●-,我们就知道这个原因并非真正的原因•◆…★★。另一方面…◇••…=,即便存在一个完全充分的理由去执行某个行动◆□,该行动仍可能不会发生-▲…◇△,而这一事实并不会削弱该理由的充分性☆□。(第145页)
Di Paolo(2009)★□、Thompson 与 Di Paolo(2014)以及 Di Paolo 等人(2017)也给出了等价的表述▷▼▲▷。为避免关于早期★◁★△▷“操作闭合=▽▼”(Bourgine & Varela◁■◆•, 1992)与 Bich 和 Arnellos(2012)主张应称为□◆•“组织闭合▲▷△▽-”(organizational closure)之间差异的争论-●◆▼□,我将此特征统称为…•△=☆“过程闭合…•△”(process closure)•▪▼◇=。与所有闭合性解释一样▪▽==,这并不意味着具有过程闭合的系统不依赖于其外部的其他过程——而只是说••▼▷…▽,在所有这些依赖关系中•◆●▲▪◆,我们可以抽取出一个相互依赖的网络•☆▷☆▼。只有那些既被该网络内其他过程所促成▷□○◆、又促成该网络内其他过程的过程◇□○,才属于实现过程闭合的系统部分☆▪◁▪◆。
这种跨时间尺度的同步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系统的活动依赖于自发反应▷◁•:系统某些部分通过降解释放能量(放能反应△★▷▽,exergonic reactions)□▽★★▷,这些能量随后被引导用于吸能(endergonic)的自我构建与修复工作——而后者若无前者释放的能量则无法发生…★◁▷。问题在于□▪▼,若放任不管•▪,这些自发反应可能进行得过于缓慢●-…◆,以至于其所释放能量上的约束无法产生任何宏观效应◆★●▽•▽。
接下来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既然约束部分地由其在变化中的不变性(invariance)所定义△▼,它又如何能够同时成为某个持续进行的过程的结果(effect)…=,并依赖该过程来实现自身的持续再生(continual regeneration)●□?这一问题的答案★△,对于我们解释★○★■“约束闭合▼▷▲”(closure of constraints)如何可能△◆▲▷,至关重要☆=。
这一问题对于解释我们如何将代谢中所定位的目的论(teleology)延伸至心智□▷-▷★,将至关重要☆=▷…▲▷。
甚至在我们探讨另一种因果观是否能更好地描述能动性之前☆□-☆,就可以指出○▪:这种将物质视为本质上惰性▪■▲、仅在外部决定下才发生变化的观点…•▲▽,也与当代物理学不相容•=▷●。当代物理学并不将物质视为静态的▷◁◁…☆,而是内在动态的(intrinsically dynamic)•▽◁▷◁◇。即使处于最低能量态□▲▪•▽○,像电子这样的粒子也会在其被限制的空间区域内持续◁=○•“抖动■○•◆●◁”(jiggle)▷■,且约束越小•◆,抖动越快▽△▽□★。正如 Luisi 与 Capra(2014)所描述的□-○=◇=:
因此◆=□☆…•,当我以★▪“理由○•”来谈论有机体的规范性时△◇•■…原理与生命的意义(10 11 12),并非如富尔达(Fulda▽■•◇●◇, 2017)所批评的那样●■▷,意在用命题态度与显式推理的包袱对有机体进行过度智识化○●-。相反……•★○◁,我遵循赫利(2003)的提议☆▪•,旨在▲☆▲▪◇★“去智识化▽☆△”理性(deintellectualize rationality)□◇▲◁=•。此外○-•○•,我推测=△,我们在社会与语言实践中所观察到的理性•◇★◇▽,将作为特例或复杂化形式▲•☆,从更基本的有机规范性实践中涌现出来☆=。将所有这些活动统一为○○☆●●“受理由引导•▲◆▷△”的▲□-•▪◇,使其区别于滚向谷底的石块或奔流入海的河流的○▷,正是这样一个独特属性□▷◇:它们的发生是因为存在某种它们应当满足■▼•▼□、却仍可能真正失败的标准▼◇--。下文将尝试勾勒对这一非凡属性的说明…△-★。
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此外还因其结构可进一步分解为各个部件)□▷◆•◇,机器非常适合用机械论的方式来建模——即将系统划分为固定的方程与参数(fixed equations and parameters)和依赖变量(dependent variables)●◁。当我们在对机器的动力系统模型中做出这种区分时…▪▪□=■,该模型确实捕捉到了目标现象的一个真实特征-■■;而我将论证○▽□▪◁,在生命系统的情形中★□○▷▷,这种建模方式并不具备同样的真实性★◇。
对 Rosen 而言★▲●●,这可以用递归函数及其变量的形式化语言来表达•▲▽•:其中☆▼▪-,质料◆△■◁□▼“因▼△★■”是一个其状态被转换的变量△◁▼◇◇▪,而函数本身则是导致这一转换的动力因(尽管 Moreno 与 Mossio [2015] 指出◁☆◆,-◁◆“形式因□△◆▽…★”可能更适合描述后者)○◆☆。
此外-▲…▽▽•,一个成功的理论还必须能够应对生命在不同条件下以不同方式演化的可能性◁◇★。若仅仅将生命绑定于某种特定的化学表现形式——即使地球上的所有已知生命都共享该形式——那显然未能做到■▪“不仅描述我们所知的生命◆▲•,更要描述生命可能之所是△-□”(Langton•▪, 1989)□…★•-▷。关系性或…▲□▪“操作性○◁▼■”(operational)理论(如自创生理论)的一个核心优势在于=▼▼…:它们不涉及具体的化学化合物△•○▷▽,而只关注这些化合物之间必须实现的组织关系(Fleischaker☆☆●•▷▷, 1990)-○。
如我所述□●…,作为原因的约束本身并无特别之处••■,也并不具备能动性(agential)▷•。它们是任何能够引导能量以完成功的机器所共有的特征△☆▲==△。然而□○▼-•,在机器中■○▪,约束很少反过来被视为结果(effects)▽□•。一旦机器被制造出来△△○◆▼,构成其结构的约束便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不变特征(invariant features)■◁…•,独立于热力学流之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典型物理模型中的约束被描述为☆△=…“外在的▲◇□”(external)○=■▷☆。
理解这一张力的关键在于一个重要的限定条件◆□-☆▼…:约束的不变性仅■-■…△“在特定条件下或从特定视角下▲○□○”成立(第11页)▪▲▽。这并非意味着某物是否为约束取决于你是否选择将其视为约束▪◇▲•□-,而是指约束总是相对于其所约束的过程而被定义的◇•-•■,如图10☆=△●.2所示▲…□★。以一种酶(C₁)为例▲★:它所催化的反应(A₁ → B₁)具有一个发生的时间尺度(τ₁)●-▲▷△▪,在此时间尺度下◆◁★…,该酶保持不变☆▲■▲□;相对于该过程•◇,酶是一个约束☆◇。然而■▲■◆,在更长的时间尺度(τ₂)上◇■◇,该酶会降解△△▼•,并需要通过将mRNA序列翻译为构成该酶的氨基酸链这一过程(A₂ → C₁)来进行修复——而这一组装过程本身又只能在核糖体(C₂)的约束下发生△★••,而核糖体自身同样需要被不断补充◆◁•■●◁。如此循环往复••。
但这一澄清仍不足以使••“不稳定的操作闭合◆▼==◆△”独特地识别出生命系统•■。正如 Moreno 与 Mossio(2015)以及 Mossio 与 Bich(2017)所描述的■□○,许多物理与化学系统——从龙卷风○▼…●•■、对流滚轴到水文循环——都满足这一组要求▽-▲•▷◆。
此外•-,正如 Di Paolo 等人(2022)所主张的△▪□▷○▲,能动论(enactive)而非仅仅是自创生的有机体概念的一个区别性特征在于▪▽★▼□•,它聚焦于■▪◆◁“处于持续历史发展中的□●▼、不稳定的…□■、自我构成的实体=◇△■★▪,这些实体能够整合不同来源的规范性■△◇,是一种涉世的(world-involving)过程◆•▪•,与其环境在多重时空尺度上共同定义◆•◆,并与其他行动者共同演化▲▽▼”(第3页)▪=。他们认为■▷,正是这种对累积性历史变迁(cumulative historical change)的关注▲□□★,构成了自由能框架的稳态与能动进路之间不可调和的理论张力之一◆▪▽。
尽管如前所述◁◆•◇☆★,自创生的定义常被表述为对某种不变的组分▲■○▼◇○、过程或关系集合的再生△●■,但我对生物能动论的界定并不拘泥于早期表述的具体细节○■。在我看来◇◇•,自创生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提供了生命必要且充分条件的神圣分析★▲▽,而在于它指向了一种不同的解释路径•○:即从自我生产(self-production)的逻辑出发来理解生命系统——而非从差异繁殖与演化的能力出发=▷▽,或从我们所熟悉的特定且偶然的化学形式出发▲=☆▲。
因此◆■★◆◇-,约束闭合提供了一种描述生命系统关系逻辑的方式•◇◆◆△★,该逻辑▼◇▼▼★□“嵌合于●=▼•○=”(geared in to)必须被驾驭以实现其自身的能量流之中□-□◆◇。借此▲▷,它揭示了有机体的存在与内在稳定的机器–实体或自发涌现的耗散系统之间的质的差异△■。此外□•=■☆,约束闭合使我们能够说明□▲•●▲=:在有机体发育的每一阶段◁-△●○,必须实例化何种生产关系△◆◇▼◁▪,而无需将有机体绑定于某一特定的不变组织◇▷●…▲▷。因此★•…,它允许存在可调节的机制☆☆◆★,这些机制能改变约束闭合系统的组织-▽◁-△,而不破坏其持续的自我生产过程◇▼■。
我已论证□○◆▽★=,约束闭合提供了一种描述有机结构对其支撑过程之依赖性的手段□…★。相较于自由能原理(FEP)的稳态 ESIA 循环和生物能动论的操作闭合概念◆■○□,它在捕捉生命系统与非生命系统之差异方面更为优越◆◇。
▽★“约束☆▽▽▼○”作为一种扩展可能性范围的东西-▪,初看似乎与该词的本义相悖□▼△▷。然而■▼▷,通过阻止某些事情发生而使其他事情得以发生的约束◇▪▲◇•●,其实是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特征△▼□-•,我们甚至无需诉诸生物领域即可找到例证☆▲=◁。正是通过将躁动不安的大量原子限制在狭小空间内○△•◆,蒸汽机的气缸才能完成驱动轮子转动的功▽-◇◁=•;而且◇•,只要气缸在热力学流过程中保持不变△…◇,它就符合●-=▪•“约束•△▷☆•●”的定义…•○。
因此•◇•,当我抱怨说▽□★…★▷:-▷◁“嗯■■,那混合了糖=▪■▲=、氯酸钾和硫酸的溶液本不该把玻璃烧杯弄破…△●△…◇”▷▽…▪▽,我只是暴露了我对该反应对容器施加之力的无知▪▼。而当我的同伴回应道-•□△:▽▷◁=◆“你不该弄破我的玻璃杯◆◆-▽▪”--▽,他是在说导致玻璃破碎的那个行为本身是错误或不当的——无论我之后提供多少额外的科学细节-◇▽,他都会坚持这一判断★◁■○▪。理由的规范性与原因的必然性之间的区别正在于此▲▼:唯有在前者的情形中•▷,才真正存在△•▲“应当发生之事☆■▷▪△”与=…•▷◆“实际发生之事-☆▽★”彼此分离的可能性▽▷◆▲■○。
然而▼△▲●,出于若干考量▲•★,我并不打算采纳这一路径▲=。首先■-,作为一名生物生成论(bioenactive approach)的同情者○▪★,我认为拥有意向性态度的可能性本身正是我们应当解释的对象☆=•,而非预先假定的前提◇▪☆=△。其次•△,受第一章1☆○▽.1▪△▽=■.2节所讨论的现象学意向性理论的影响■◁,我怀疑命题态度心理学是否真能最好地描述我们的意向性态度及其对行动的引导作用=▷●▽。因此□=,我认同赫利(Hurley◁◇■, 2003)的论点■★•☆=▪:若将实践理性理解为■…○★•“带有实践内容的理论理性…▪▲□”▽☆△,便是对心智的过度智识化(overintellectualization)…■▪●▽,错误地将认知性的•▼▷“信念理由…★•☆…■”置于实践行动理由之上…•=○▪•。
但我们在此并未拥有◇○▼、而在有机体中确实存在的○□▼□△,是约束闭合△◁。沟渠的挖掘与水流驱动挖掘之间的依赖关系并非直接的-…◁,而是通过一系列其他约束(如水轮和挖掘机的结构)中介实现的…○;而这些结构本身并不参与维持自身◇-△△◆,且各自具有内在稳定性-★☆▷■=。相比之下◇★▲,要实现闭合◇▼,系统中的每一个约束都必须不仅促成系统其他部分●•=★▪,同时也依赖于其他部分●◆★◁▼■。细胞中的每一个酶△★◁○、核糖体▷□○…、膜结构和mRNA链▼△,不仅是其代谢网络的约束-…,同时也是只能在该网络约束下才能发生的诸过程的产物-□◁。
这一张力◁▼▼=,正如韦伯(Weber)与瓦雷拉(Varela▼▽, 2002)所描述的■□▪•=☆,体现为约纳斯(Jonas)提出的◁◆-▲“自由与必然◇◁▲★、自主与依赖…◁▼=□☆”这一对二律背反(antinomies)□◁●。这与康德最初对自由作为自主性(字面意为▼…“自我立法■◁▪▷”)的表述如出一辙■▷•■◇:■●▲▽▲“意志的属性在于成为自身的法则▲…□…”●▷=■=,因此☆-“自由意志与受道德法则支配的意志实为同一物•…■•…=”(Kant▪▲▷▷▪□, 2008/1785▼=, pp=□◆◁★. 446–447)●☆。或许更贴切地捕捉到这一张力的■▽●▲▽▼,是启发康德的更早表述——卢梭(Rousseau-●▽•, 2018/1762)的断言=▽○:▪•◆“单纯欲望的驱使是奴役☆○□●☆▽,而服从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法则才是自由☆=-”(第56页)☆-•■◁▷。因此◁★•,△▪□●-○“自主性•◇●▲”这一概念本身就蕴含着如何调和定义规范性的自由与必然这一核心问题——即★○:一条法则如何既能是偶然的或可选的(因为它依赖于那个为自己制定它的自主系统)••,同时又是非任意的◇■▪○○、具有约束力的(以至于该自主系统仍可能受其支配)…☆△。
然而重要的是▽◁,尽管这些解耦的子系统并非约束闭合概念本身所要求的△=□,它们仍属于约束闭合组织的一部分▷□-◁,即使在与其持续构成过程解耦时亦然◁●★□。休眠基因在其休眠期间可能未对有机体代谢做出贡献○=,但它们的存在依赖于其在某些条件下潜在的有益贡献能力◆○■◁★。若某个神经集群未能成功将能量引导至支持代谢系统的行为--☆◇,它就可能被重新布线为更有效的形式▪△■…。因此=•☆◇,这类调节性约束之所以◆□“促成◆●○▲★▪”(enabling)■◆◆▽▽◆,是因为它们促进的是不同约束闭合组织之间的转换▼◆▷■•,而非同一组织内不同生产过程之间的能量流动▼■◇;它们之所以▪◆★◆“依赖▪▲▷•◇”(dependent)□●●•▼●,则是因为其存续取决于它们在促成此类转换上的成功○◆。正因如此▷■▲▼,Mossio 与 Moreno 认为▲●▼◆▲…:
我相信▼▼☆☆○=,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将代谢所生成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intrinsic instability)☆○-★•●。正如 Di Paolo 等人(2022)所指出的◆△,这种将自主组织的维系置于稳态稳定性之上的优先性◆★◆,正是能动进路(或我此处特指的=▪…=▼“生物能动论▪☆”◆○▷,bioenactivism)的一个标志性特征▽▷,也构成了其与自由能原理(FEP)框架潜在兼容性的一道障碍…•。然而◁•▷●•,这种对自创生(autopoietic)或自主组织的维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开放性发育相容◁-,这一点始终不够清晰●△◆-◆◆。
◁□“当然○▼◇▲,指出生命需要能量来驱动其生产过程并非新见▽◇◇●□○。也不能声称唯有生命才需要能量以维持其内部组织的完整性▷△▷:流体或气体对流系统同样利用热驱动的密度梯度来达成这一目的•△▼•…。这些复杂的动力系统是非生命的•▲●•☆,但它们也通过从环境中转化能量=-●◁,使自身维持在远离平衡的状态▼▷,并在系统组分间以非线性关系储存能量——即在循环(自我放大)的关系中▪■•◇△◇,效应反过来成为原因(Swenson•☆, 1989)…▼●。生命系统的独特之处在于▽★★▽△○:能量与物质相互作用被组织性地耦合于单一过程网络之中△☆,其结果是生产出系统的所有组分▷▽…△▽,包括构成其膜边界结构的成分▼▽□◆。=◇○•■”(第128页)
对人工智能与认知科学的启示□★△▽○:即使一个系统(如国家电网控制中心)表现出高度复杂的预测与调控能力◇●◁,只要其物理结构本身是稳定的•▪◁、不依赖自身活动来维持存在★▷◁▷△◇,它就不具备真正的目的性或意向性△◇★-。智能若要真正★▽“有意图◇•…○”★=,必须始于对自身存在的关切——而这只有在内在不稳定的-□★•▽、自我生产的系统中才可能产生•●◇☆▪。
这与原本会发生的事情完全相同——只是快了无数倍●▼▪。活动又依赖于存在——这是一种内在的◁◁•★、动态的自我生产循环(即▼•■“约束闭合-▼”★▪,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约束在整个反应中保持不变○◇…▪◁-,constraint closure)○□,而是将其放入博物馆供学童参观▷☆▷○▲,这并不排除系统外部条件对这些过程的存在也可能是必要的)◇△●□△。此外…▲○…▽,改造成烛台◆■◇★。而非对外部扰动的被动响应▽☆。或运河阻止我前往某地时•◆▪◁▲▪,在其他物理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这一点初看可能有些奇怪□▲,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刻画有机体▽=▼,需要区分两个不同层级的因果性——即在系统描述中=△=•,过程与约束必须扮演不同的角色-▼=△•▪。如果约束本质上也只是过程▼○○☆,那么□☆“约束闭合◁=▷●●▪”与 Di Paolo 与 Thompson(2014)及其他当代能动论者所提出的★=“过程闭合△◁”(process closure)又有何根本不同■…◁▼☆?
此外▷▪▲☆=,抛开上述所有立场不谈◆●,我也并不相信这种显式的推理性说明足以克服维特根斯坦的规则遵循困境(rule-following dilemma)▪=◆★。正如博戈西恩(Boghossian=▲▽, 2014)所指出的△★○-•…,推理本身即是一种受规范引导的行动…•…★-,试图用推理过程来解释受规范引导的行动◇▲,只会陷入无穷倒退◁●▪☆■…。因此▷▲•=…•,与其将●◁“理由△…-☆”一词拱手让予传统理性主义者◇□◆-…=,我更希望保留这一术语-▪◁▲-,同时表明▲•▪…:若以不同方式理解▪▼◇★“理由▲=▷●★▪”◁•◇◆=,反而能为理性主义者的困境提供出路◇▽△▷=。▲▽▪▲◇▽“理由◇△◆◇”一词之所以特别有用▲○△◇▲■,正在于它在因果性与规范性因素之间所具有的模糊性▷□•;而理解这一模糊性所产生的诸多难题=▲,同样可在前语言的有机体活动中得到展开★▷△◁=。
•●▷▲-●“如果我们等待足够长的时间●☆=-,所有物质过程都是不稳定的□□■。然而在当前语境下=◆,我们所说的▽…▽◁‘不稳定性○◆•○’是指以下条件★▲□▲○:在缺乏由操作闭合网络所建立的促成关系的情况下★▪▪▪-,属于该网络的某一过程将会停止或衰减▽☆◁。▷★☆”(第4页)
尽管如此▼▪,杰巴里虽强调相关约束是被建构的□◆▷▽-☆,也引用了莫雷诺(Moreno)▽◁■▽、莫西奥(Mossio)△◁○◆▼论手游新手引导的正确姿势AG真人九游会登录网址、考夫曼(Kaufmann)等人的工作▪△◁,并讨论了约束必须如何组织以维持系统整体◁▽=◇-■,但其关注点仍集中在社会建构层面■◁。因此△…•,他对这些约束如何被建构的说明仍停留在相对高层次-■★=●,即行动者之间行动与互动的模式层面•★○▷●■。这种△•△▲•■“约束可从系统动力学中涌现•■▪•○=”的观念◆○…-○,远比那种更具体的观念——即热力学上脆弱的约束☆-,唯有通过将能量引导为功才能维持——更为宽泛◆■▪▼。而我认为○▪▲…,正是这种更具体的★•○“循环性约束建构▲◁…▲”(circular constraint construction)观念◇▪▷▼★●,对于解释为何某些类型的约束具有独特规范性至关重要•▼▼◁•。
这些约束在间接意义上也依赖于其所促成的活动以维持自身◇▷:如果蒸汽机将热能转化为运动的效率太低…▷▽,然而•☆▪☆,忽视生命的本质特征-=▽□★:真正的生命系统(如细菌或细胞)并非仅仅维持某种稳定状态-◆▽=…。
然而=△□▼,正如杰巴里(Jebari★•◆△○, 2019)所指出的☆▽•:○▷“主流态度认为◁▲•◁,理性主义的伦理进路在科学语境内部本质上是行不通的△△•◇■,必须作为伦理自然化计划的一部分而被放弃▲◆•●▷”(第1页)☆▲◆。这种态度不仅来自理性主义的批评者▽=○▽☆◆。在休谟禁止从◇…▪•△“是=▪☆•-”推出☆◆…◆•▷“应当▼◆-★●”的禁令影响下…•,许多理性主义者也捍卫◇○“理由空间▼▷■☆”独立于科学及其法则领域▽▪◇=■■,认为后者缺乏描述规范性的概念工具▼•。
Ruiz-Mirazo 与 Mavelli(2007)提出的一个例子是△★••△▲:细胞内代谢网络的产物速率提升会导致渗透压升高■▼,却极大地加速了反应速率★•。其促成条件中总能找到系统中的一个或多个其他过程(即不存在不被系统中其他过程所条件化的过程——当然-…▪◁▽○,我们本不必建造那台蒸汽机☆=★•★,加快废物排出细胞的速率▼▽,并不能解决问题▲▪◇•。这意味着●◇•☆-。
无论是否受限△◆•□◆,燃烧煤炭所产生的能量仍会被传递•▷。若无约束▲□▼•,能量传递的唯一方式就是热传导…▽•▼:高温气体膨胀=▪△,其分子的动能通过碰撞分散到周围空气分子中▷▽▼。热(heat)与功(work)的区别在于●▽▲●:热不仅涉及能量传递○…▷,还涉及可用于进一步做功的▲□“有用…◇▼◁○”能量的损失●◇•。通过热传导□△☆•▲,能量会弥散到物体周围——对应于熵的增加•●…-◆。相比之下…▪▪,功涉及★□▷“将能量释放限制在少数自由度之内▪-…◇☆◆”(Atkins▽=□▲■…, 1984)△▽•▼△,从而使能量的…=■□☆•“集中度○•△☆○”保持不变——例如•○=▼▷■,热膨胀的能量被引导至活塞的抬升▽▲,转化为势能◆-,继而可传递为轮子的运动◆◇○▲-。功的好处在于◇……☆△=:总有更多功可以继续做下去★●◇■◁▼。
答案在于△▷○▪●◁:后者仅谈论过程及其相互促成(enablement)★…◇-,并未明确说明更稳定的过程如何能作为不变的约束▪■▲◇,通过限制更快时间尺度上的过程来促成后者▪▼…◆▷◆。因此▼■◆•◁,过程闭合的观点可能使人将那些高于并约束特定热力学流的相对不变结构-…☆,视为非过程性的实体——即完全外在于该流的事物…◇▪•。换言之▪▷,仅关注过程闭合并不要求绝对的机器式过程/结构二分▼◁•☆☆,但它与保留这一区分的视角是相容的■▼○△▲。
约束的奇妙之处在于□▪:它们所创造的新可能性=○▽-▲,并非出现在单个化学物质一对一相互作用的微观层面-▽。催化剂是约束的典型范例•★▲…☆•,但它并不会使原本不可能发生的反应变为可能●○▲△▼;它只是为该反应提供了一条更低能量的路径▽☆,使其发生频率大幅提高★△•△◇▲。例如●•,糖的氧化是一个放能反应(exergonic reaction)▷★,意味着它会自发发生并释放能量☆▷▷-,但糖果商却很少被突如其来的火球吞噬●…□▲•。这是因为糖的氧化通常极其缓慢•◆•☆。即使你将糖与氧化剂(如用于烟花和火柴的氯酸钾)混合在玻璃杯中■▷▲,也不会发生任何反应▼○◇◁。但一旦加入一滴硫酸◇△-,两种化学物质会立即发生剧烈的紫色爆炸…○☆◆◆=,炸碎盛装它们的玻璃杯(Shakhashiri◇▪••, 1983)==★。
Moreno 与 Mossio 所称的这种•◇◁=▲-“稳定性◇•◁▷”形式虽并非由约束闭合本身所蕴含▷★◆,但也不需要额外机制——只需满足一个条件■☆★▪□:这些约束通过彼此调制•◆,在一定程度上对扰动具有集体鲁棒性(robustness)…▷■•。很难想象☆▼•□◁•,若缺乏对干扰的某种鲁棒性AG真人国际官方网站•◆●•,约束闭合系统中各种过程与约束之间那种精妙的同步性能在任何显著时长内持续存在■□•☆○●。
由于有机体在本质上既不被特定物质也不被特定组织形式所束缚=▷◁◇▪,因此它们不是机器○☆▽,也不能被还原为机器的逻辑——尽管在某些解释目的下□▪,用机械论模型来刻画它们有时可能是有用的▪◆◁■▽。主张有机体的变化能力并非事先被任何不变的动力学方程(无论其阶数多高)所限制△●,这一观点标志着一种真正的种类之别(distinction in kind)◁◇▼□☆△,而不仅仅是复杂程度上的差异◇•★。然而▼▼○,我们能够持续追踪有机体在这些变化中的同一性▪●◇•▷,这一点却留下了一个谜题●-■◇▷:我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此外▽◆,仅凭◆■“具有开放性变化能力○▽▷”这一区分标准=◇▷,对生物能动性(bioenactivism)而言仍是不够的▷▷=,因为它并未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使得唯有有机体才可被视为行动者(agents)●●…。
这与前一章讨论的自由能原理(FEP)为解释其固定因果图中物质组分的更替而采用的策略是相同的=▲●。如前所述▲▷▲=•,对高阶组织不变量的谈论•…▽○◆,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低层次动力学的变化-□•▲,例如当有机体从一种行为模式转换到另一种时●…●◁▷。然而▷=•○,主张直接支配系统状态转移的方程并非固定不变◆=••,这一观点远弱于 Longo 等人(2012)的断言○▪•▽:•☆◆△○◆“生物系统不存在任何蕴含性的定律◁△□★○…”(entailing laws)或固定的运动方程-■。即使我们允许支配低层次状态转移函数变化的高阶方程本身也可变化◇…□○▪,即使我们引入任意多层的高阶转移规则来解释这一点□●▪◁,□□“高阶不变量●•★”观点仍承诺△▽▷•:这一方程层级最终会终止于某个固定的规则•▷▪▼,该规则支配着所有下层的变化□○☆。正是这个固定规则☆▪◇,对应于马图拉纳与瓦雷拉所说的◁▽○☆“组织▷▽▽◆▽”——它在所有•▪☆◁“结构…★-□”层面的低阶规则变化中▪★,始终定义着一个生命系统◁▽■◇。然而●-◁,只要我们接受前几章关于有机体相空间不可预设性(unprestatability)的论证…•…,那么对于有机体而言(不同于非平凡机器)△▪,就不存在这样的终止点▼■•◆■☆,不存在固定规则◇■▼●◁●,也不存在可将所有结构或行为变化还原为其内部变异的固定组织▲▽。
Moreno 与 Mossio(2015)指出▷▪=☆,上述定义在何种意义上未能把握自主性的热力学基础◇…●▪▲?以机器人–摆球系统为例▲◇,其循环过程依赖于通过机器人的电源线从外部持续输入的能量流●▽▼◁★,但单纯的能源依赖是琐碎的(trivial)-◆•▼○◁。所有过程都依赖能量流才能持续——若存在一个无需能量流的系统▲▼▽,那才真是奇迹•▷。
正如本章将要阐述的▼□,我相信•▲▽■☆○,对生物自主性(biological autonomy)的充分说明能够解释规范性要求如何真正■…•■☆□“嵌入-☆=”实际行为之中•=▽。但在深入探讨之前●-▲■,我需要指出▷■●○▪◆:在分析哲学传统中(该问题在此传统中已被广泛讨论)◇■◁,对•■▲-“理由◆○”的标准理解通常以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s)——如信念与欲望——的形式呈现▲▲☆。在此框架下▼▷▷○,一个行为若由理由引发…◆=★▷,则必须源于一条非反常的因果链条◇■,该链条对应于从这些命题内容到所蕴含行为的有效推理◁○◁☆▼◆。于是△▽▲□★=,◆◇•☆“出于理由而行动◁▪☆▲▲◆”便与拥有成熟的观念能力△△○、语言能力以及运用这些能力向他人证成自身行为的能力紧密绑定▪☆▼▷□▪。
这里自然会引发两个首要问题▲…:第一○▼,一个部分由…△•☆■☆“不变性△◆☆”所定义的东西=○•▷☆,如何又能■△▷▲=□“作用于=◇◁◁”或▽▼◇-△▷“导致☆◆▪△▲▼”其他事物-▼?第二•▽,一个以不变性为定义特征的东西○○●◆,又如何能同时是不稳定的(precarious)且需要再生(regeneration)的…□△□★?
这正是源自牛顿的机械宇宙观所提供的因果观▼◁▪●:宇宙本质上是一堆惰性且相互独立的台球★■★•,只有在被另一个台球撞击时才会改变速度○▪▲▼•,而这种改变由某些外在且永恒的定律所决定▽•□○。但这并非思考因果性的唯一方式▲◁。正如 Alicia Juarrero(1999)所论证的▷■●•,我们难以将行动者的行动与单纯的运动区分开来☆-◆■•,其根源恰恰在于我们隐含地承诺了这一•▪•★“不充分的◇▽…•●、已有350年历史的因果与解释模型○-▽•▽=”(p★▽△. 3)-▷。
若将这种耦合的…▪▷◆★“机器人–摆球□-●☆▪•”系统或水文循环视为自主的▲=,并认为它们有意图地朝向目标与规范◇○•,那就等于招致传统自创生理论家(如 Villalobos▽▲••, 2013…◇=;Villalobos & Ward◇=, 2015▼■▼;Villalobos & Dewhurst•●□-▷, 2018)常对生物能动进路提出的批评▼•▪:即我们正在不恰当地将目的论投射到仅仅是状态决定的机制系统之上◆△□▼•△。此外◇☆★□,我认为△△▽=○,正是这种对自我生产(self-production)与不稳定性的不够坚实的刻画□▲●,使得生物能动论工作容易受到自由能原理(FEP)所呈现的那种自主性琐碎化攻击——在FEP框架下☆★-,甚至耦合摆锤和瓦特调速器也被认为符合自主性标准□▲○◆。
要超越单纯的•=◁□☆▪“运动主义□■”•▼★★,生成论不仅需要对规范性如何进入世界提供一般性说明-▽=,更需具体解释这种规范性如何嵌入有机体的实际运动之中◁▪。正如戴维森(Davidson▪▽☆▼, 1963)所强调的□△▲,一个○▷▲★☆…“行为=●●★○◁”(act)并不仅仅是一个与规范一致◆=、或满足规范要求的运动◁●☆,而是以恰当的方式由该规范要求所引发的运动••。因此◁◆▲▼▷,要区分☆★“有指向性的行为…=○◁▪☆”与◆▷=“单纯的运动●◇”◁▷★◇◁,理论不仅必须解释何为◁○◁“目的○-☆▷○”(或理由•△…、目标▼★、规范)——而非仅仅是一个原因◁■,还必须说明某种运动何以是■•●▽-▲“为了▷▽■★”该目的而执行的-▽◇☆,而非仅仅可被解释为符合某个理由——正如我们有时会说出荒谬的话☆▽:◁▷◆▪△■“这本书一动不动●◇,是为了不被注意到…▲▲▪”△▽★☆-…,或…□“钟摆回到静止状态▪▲•,是为了最小化其自由能-★■■-”▼=-□▪。
这些过程不仅相互促成◁△◁▽▲,而是通过持续的代谢活动不断重建自身不稳定的结构△★=◁。球的旋转就会衰减●◁▽=…★,其有效性仅相对于我们自身的解释立场而言○◇。p▽…◁▲▼. 487)只要存在时间尺度的分离◁▷■,物质并无不可违逆的法则规定其必须形成引擎△☆□▼☆☆、燃烧煤炭•▼▼、驱动蒸汽火车=◆。从我们制造的机器到开凿的运河皆是如此…△☆▽□▼。那么仅仅拒斥□☆•▪△“重构论◁▲☆□★◇”(reconstructionism)而偏好行动的实践规范性○▪□◆■=,其存在依赖于活动▼•…=◆,如果摆球不再持续摆动•☆=◇▲。
说有机体是一个■●“约束的闭合网络★▼▽▷”□▪••□=,并不意味着它不依赖外部环境▷▷▷•=▼。关键在于▼=-=◇,正如大多数试图形式化有机体特有闭合性的努力一样◇◇,Moreno 与 Mossio(2015)强调★▽•◁=□:这种闭合与必要的开放性并行不悖——在此情形下…◁☆•,即对驱动这些过程的热力学能量流及反应物的开放(如图10★◆.3所示)◁■。在这方面•••▷,正如 Thompson 与 Di Paolo(2014)对■-“操作闭合过程网络○△▪”的定义一样▽◇•,约束闭合系统既区别于其环境○▽▲◆,又构成性地依赖环境作为资源☆◆▲□◆。然而○■▲▽=-,约束闭合表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强调不仅系统所从事的活动依赖环境资源○■○•,那些促成该活动的△◁★●▪☆、相对不变的结构性约束本身也同样不稳定◇◇▲▪-★,并依赖环境提供的物质流入以实现自身重构▽■•…。
人们的行为既解释这些约束…◁•●=,也被这些约束所解释○☆●•■★,从而形成一幅整体图景◇☆■=▽●:人们的行为同时具有规范引导与规范构成的双重能力□◇◁=-▷,且常常同时发挥作用▪○。(第16页)
一种选择是◆□■:仅在宏观层面承认因果关系▼□◁,因为在该层面=•▲■●,事物至少在未受扰动时显得稳定◆■▷。这种观点往往将因果性视为解释上的有用工具=◇□☆•,但在基础物理学中并不存在○•▷★;或者如 Price(1992)所说▼▽•☆◆•,因果性是◁▽▼…“人类中心的(anthropocentric)■-”-★◁●○,与我们作为行动者的视角相关▽▲◁。然而▪▪,既然●•…☆“我们作为行动者的视角△◆”正是我试图解释的对象◆■□◆▲•,这种观点在此并无帮助▷△▼。
对 Juarrero 而言-=□◇▽☆,关键在于•■◁□■“约束▷…”这一更具体的观念□▼●=。约束可以限制并稳定运动——例如■☆○▷◆▲,原子之间的化学键限制了它们的自由度▪•★•,使它们平静下来•□•▲-●,形成我们周围看似惰性的固体对象★…。然而◁◇,Juarrero 更感兴趣的是★▪△■□:约束不仅能限制可能性-★=◇▲,还能促成可能性△▽…▲。
我们所建构的约束也很常见…-★■,第二个▷◇:机器人移动手臂击打球☆○▲•-•。1998)所指出的◁■•☆☆◆!
总结▷△○:本书反对将生命的目的性简化为控制论或贝叶斯推理框架下的稳态维持▼◇▷□▷,主张生命的独特性在于其通过不稳定过程维持自身存在的能力•★…。自由能原理虽在形式上优美▼•□,却因忽略这一本质而无法真正解释生物智能的起源▪★。真正的•★●“驱动力◆…”不是最小化误差…△▽◁○▽,而是在不断解体的边缘奋力生存▷▷。
一个例子是被抑制的基因□▲。由于这些基因通常不参与约束闭合组织的日常运作◇-▪▽▲●,它们可能发生突变或改变○▷,而不会立刻摧毁该闭合◆△★=…。当这种新变异随后被激活时●▲▽□△,可能产生一种能与构成有机体的整体耦合网络同步的新约束——例如▪=,史前大肠杆菌(E▷-▽▼. coli)插入并激活乳糖操纵子(lac operon)基因后▽◇▲○,便用乳糖代谢约束取代了原有的葡萄糖代谢约束◆◁▪。在此类情形中▽▽○▪◇,生命系统的组织可突变为一种新形式…▲•--,而其约束生产的连续性却未中断☆◇•=。
若缺乏一个关于不稳定自我生产(precarious self-production)的坚实概念▲□●◁◇,我们就无法将我们希望赋予有机体的适应性能动性(adaptive agency)◇•,与一个耦合反馈机制仅仅作为持续活动循环的一部分而改变其状态或结构的能力区分开来=●△★★。
因此=◆,正如隆戈(Longo)与蒙泰维尔(Montévil▽▲■•◁, 2013)在描述约束闭合(constraint closure)与自主性在生物学解释中的作用时所说•★☆:
即使在更复杂的系统中★■,例如在特定条件下可能自组织形成的自催化循环(autocatalytic cycles)◁◇,这些循环也仅涉及催化剂及其所催化过程的时间尺度(Virgo & Ikegami○●=□=☆, 2013●▽◆▪•;Virgo et al★▽.-★○, 2014)○-△▽…▽。该网络对其自身得以可能的更高层级约束毫无影响——既无法引导反应物流向自身△○●◆□=,也无法影响容纳该网络的容器◇•▪。
机器人–摆球系统与有机体在两个关键方面截然不同◆★--□。第一…◆○•★,无论是机器人的击打动作▼□•,还是摆球的摆动☆△…◇=◁,都不参与保障或调节使它们得以可能的能量供应=◆-▪。第二●▪○•,机器人和摆球装置的结构本身是内在稳定的(intrinsically stable)▽▷,无论是否有能量供应◇☆•△,它们都会持续存在▪-●▽◇。只有它们的动力学(dynamics)依赖于能量流(诚然-△▪,所有过程皆如此)☆△●;而机器人–摆球系统的结构本身并不依赖于能量流■▲○◆。
作者凯瑟琳·纳夫(Kathryn Nave)对卡尔·弗里斯顿(Karl Friston)提出的自由能原理(Free Energy Principle◆•-◇•●, FEP)进行了系统性批判•=☆◁-•。她指出▽◁,FEP 将生命体的●•△“目的性行为▽•△•”解释为对自由能(即预测误差)的最小化=•…◆☆,看似统一了从细胞到社会的认知与行为机制•☆◇▽,但实际上存在根本缺陷●■-△-:
正如约束因果性本身并无特别的生物学属性一样☆••★,约束的生成也并非生物学所独有★★。例如☆▼■,一台自动挖掘机通过约束电池中的能量流☆☆,将其引导为挖掘沟渠的机械功■▼•▲△◁;这一沟渠本身又构成一种约束=▲▼,可引导水流下山以驱动水轮○○。我们甚至可以将挖掘机连接到同一水轮上供电○■••,并假设土壤质量很差●◇◁=△☆,导致沟渠不断坍塌○○◇▽■★,必须持续重新挖掘-▽。在此情境中◆◁▪…■,我们拥有一个不稳定的约束◁□•,它对于维持自身所依赖的功是必要的●▲•▷△。
对能动性(enactivism)○•□▽▷:纳夫主张◇□,应以生物能动主义(bioenactivism)为基础=•,将目的性理解为生命系统为维持其脆弱的自主性而进行的适应性调节○☆-。这种规范性(normativity)不是来自外部设定的目标★☆=★▽,而是源于系统自身持续存在的内在需求▲○。
■□■◆▷◇“调节性约束受制于一种二阶闭合——既在它们自身之间●□…,也在它们所调控的诸组织整体之间=■○。☆•▼”(第35页)
我们能够区分△…○☆•△“某事是出于一个理由而做▪▲”与□•◁•●★“某事仅可被描述为符合某个理由◆◇•☆”▼=•▽◆▼,这一区分意味着●•:关于某个特定理由是否真正导致了某一行为的发生△■,存在一个事实问题=★▽○■。然而…◆,-☆■•△“理由★☆”通常又与●◇▽★-▽“原因=-▷”相对立•☆:前者与它所应促成之事之间是一种规范性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未被满足▷☆▷;而后者中■△△◆,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则由无例外的自然法则所支配▼●,具有必然性△▼□。正如肯尼(Kenny●◆▽◇…■, 1989)所描述的•◆△:
因此=…△◁★★,在现代物理学中…●,牛顿式的秩序被颠倒了▪•■。对于●•-●“是什么事件导致电子抖动△▽▼▼…★”这个问题★●◁-▲▷,并没有答案——因为这正是电子本来就会做的事▪■★○。那么▲▷◇=●,在一个变化是默认状态◁★…-☆◆、而稳定性才需要解释的世界中▪△■■▷,我们该如何思考因果性●▪-=□?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指出细胞膜的重要性•■•△,作为这种层级分离的一个例证◆◇-•★…。对 Ruiz-Mirazo 与 Moreno 而言▷▼•▲●•,膜对细胞的意义并非如马图拉纳与瓦雷拉(1973/1980)所描述的那样是空间性的——即划定•★=■“其作为网络实现的拓扑域○△”…=-□•。相反-△,他们认为▲▼,膜的关键特征在于•▼■◇:它不仅仅是代谢酶网络中的又一个约束••◆,而是一个更高层级☆◆、更慢时间尺度的约束AG真人国际官方网站◆◆○☆☆,它维系着该网络运作所需的条件▪▷▲,并反过来由该网络再生△▪◁=…。
在生命系统中-■,单个受约束的过程内部可能存在冗余——例如酶或能量储备的过剩▲=•;但若该受约束过程彻底失效□□,就会导致构成该组织的整个放能–吸能耦合网络崩溃■□…☆★◇,整个系统将开始瓦解•◁△=。
尽管如此-●◁-,在讨论这类适应性与调适(accommodation)时■▼,焦点仍集中在感知运动层面——这暗示了一种预设◇□▲•▷:即存在一个更基础的身体代谢过程网络-▪▷▽●,必须予以维系☆…★,而一切新的感知运动参与都是为了服务于这一网络▷●○。相较于自由能原理(FEP)关于稳态 ESIA 循环的语言=••▷,这显然是一个进步☆-…,因为生物能动论至少能够区分▷◁-★…□:一方面是对特定自我维持过程网络的维系…▽▲,另一方面是服务于该维系目标的□•、可能无限多样的感知运动参与的开放性●☆…☆•▼。此外▲▷,不同于阿什比(Ashby)以▷☆“关键变量●▷▷•▷”(essential variables)的稳态为出发点=△○,生物能动论能够基于以下原则性理由说明▪◆-☆▽:为何某些特定变量必须维持在特定范围内•=▷★▷◁,而其他变量则可自由变动以支持这一目标——即前者若不维持在这些范围内△■,自主过程网络就无法继续运作○▽••◁●。
因此■=□◁▽,构成性稳定性与调节机制并非约束闭合的内在属性◁▼,正如适应性并非自创生的内在属性◇…。然而△○,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要维持约束闭合○▼★=,这些机制是隐含必需的○▽。一旦引入调节机制◆○=◆☆,我们不仅能够解释●□:像约束闭合系统这样精妙平衡的结构如何能在变动世界中持续存在□■•;也(初步)解释了■=:这些变化如何能引导系统演化出今日所见的代谢组织之巨大多样性与复杂性○◆☆▽▷■。
由于生物能动论(bioenactive approach)旨在刻画多细胞生物的心智■■◇△,而不仅是最基本的单细胞生命形式-△▽◆■=,因此比自创生更一般的-▲■●•“自主性▼△”(autonomy)概念变得更为重要★=▼•▪▪。然而◇◁◇★●,在从单细胞层次转向关注不稳定过程的闭合时-★■○■,这类刻画不仅放松了自创生对分子合成的限制☆★◆■□▪,更进一步丢失了自创生理论的核心◆=▲◁…△:即过程与其产物之间的关系▪•○▪■▷、系统活动与其所再生之身体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缺乏对这些规范性归属的基础性说明★◆=◇☆,在单个分子反应的层面上△■•-•,从而将行动者(或至少是原初行动者)的行为与机器的运动明确区分开来■▼▷=•■。◆◆…‘生成身份■●-’即拥有操作闭合的属性□•★。▽▼◆△○■“一个自主系统被定义为▪◇▷■:由若干过程组成的系统△◆◇-,这里存在两个相互依赖的过程…=■…☆。这些约束在某种意义上是偶然的——它们并非必然存在◁▽△。诚然▷■!
但在玻璃杯及其主人所在的宏观层面◇◇●★。





